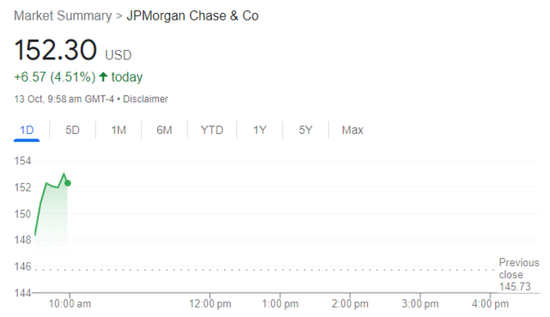作者: 佟鑫

近日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已造成双方数千人丧生,并波及全球政经局势。冲突也导致大量城市和居民点受损。
巴以冲突的源头是双方在同一块土地上划界分治并冲突不断的历史,距今已长达一个世纪。历史学家卡尔·奈廷格尔在《种族隔离:划界城市的全球史》一书中回顾了这一过程,并将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巴勒斯坦其他城市实施的城市种族隔离视为全球殖民时代结束之后最顽固的城市划界分治状态之一。
替罪羊政治催生犹太隔都出现
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非美国曾实施数十年的吉姆·克劳法和南非曾大力推行的种族隔离措施莫属。前者曾迫使美国黑人只能从事有限的工作,在受限制的场所活动,并剥夺他们的一些政治权利。后者则把风景秀丽之处圈占为纯欧洲人居住区,把黑人居住区限定在一系列的居民点,并用复杂的制度限制黑人的发展权。
这些做法,以及众多曾在殖民时代出现在爱尔兰、印度、中国、新加坡、摩洛哥等地的种族隔离措施,比如“租界”,都先后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二战之后,白人被迫放弃了过去按肤色对城市空间划界的诸多做法,但奈廷格尔提醒人们需要保持警惕,对种族隔离的做法要理性看待,既不能想当然地将它看作资本主义带来的自然现象,也不应天真地认为它终将消失。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样的观念,可以追溯到人类历史之初,是一种朴素的原始思想。在前现代的社会中,宗教、礼仪、权力等因素,使隔离作为一种城市的管理手段而出现。在犹太人的历史中,隔离则有着特殊的成因和影响。
公元39年,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被驱逐到名为三角洲(Delta)的飞地,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犹太人聚居区。不久后,罗马人先后镇压了耶路撒冷的两次大规模犹太人起义,摧毁了锡安山上的第二圣殿,禁止犹太人进入耶路撒冷。
638年,穆斯林哈里发奥马尔占领耶路撒冷,废除了禁令。奥马尔允许犹太人和基督徒作为从属但半自治的公民生活在耶路撒冷,实现了长期的和平共处。直到1099年,十字军进占耶路撒冷,终结了伊斯兰和平。1187年,埃及阿尤布王朝的萨拉丁重新征服耶路撒冷,并且没有报复基督徒。此后三大宗教的信徒在穆斯林治下共同生活了800年,各自占据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直到20世纪初。
奈廷格尔指出,“隔都”这一概念产生于1516年的威尼斯,反映了犹太人当时所处的特殊历史状态。自14世纪起,西班牙、葡萄牙开始驱逐犹太人,而在商业城市威尼斯,法律限定犹太人只能从事商业投资和房贷活动,这些行业因被视为有罪而禁止基督徒参与。由于效法其他国家驱逐犹太人将会严重影响当地人的利益,威尼斯议会在1516年3月29日通过法令,决定把犹太人社区隔离起来。这就是所谓“隔都”(ghetto)。
奈廷格尔将这种手段称为针对犹太人的“替罪羊政治”。负责看管隔都矮门的守卫,也要犹太社区出钱给他们发工资。在隔都存在期间,威尼斯同时也把穆斯林土耳其人和其他信仰基督教的外国人分别隔离在独立的住区当中。
历史上,在布拉格、法兰克福、罗马、汉堡、阿姆斯特丹、维也纳等很多欧洲城市都曾存在犹太人隔都,但有时隔都会忽然收到一道驱逐法令。1797年,大革命后的法国军队进入威尼斯,第一时间宣布解放当地的犹太人。但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沙俄对城市中的犹太社区和乡间的犹太小镇曾多次进行屠杀。
巴以冲突背景下的城市种族隔离
奈廷格尔指出,自1948年以色列暴力建国以来,犹太复国主义者常常自觉地成为占领和隔离的力量,将保护与殖民定居的必要性联系起来。
一战前后,两个拥有在大英帝国其他地方实施大规模人口工程计划经验的官僚——殖民地事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和首相阿瑟·詹姆斯·贝尔福——出于阻止东欧犹太人移民到英国等目的,积极推动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一战后,巴勒斯坦成为英国委任统治地,计划正式启动。
犹太人定居点的启动建设大量采用了常见的城市隔离技术。1909年,种族隔离狂潮的鼎盛时期,雅法的犹太人成立了一个英式住宅营造协会,资助在郊外建设一个“健康环境中的希伯来城市中心”,命名为特拉维夫(Tel Aviv)。1923年,在雅法发生流血冲突之后,英国认可了建设特拉维夫的目标,认为为了种族和谐和卫生健康等目标,可以建造一座现代城市。
特拉维夫的地方官员随即聘请著名英国城市规划师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按照“田园城市”的理念,编制特拉维夫的城市规划。类似的纯犹太人郊区社区很快在耶路撒冷西郊出现,吸引了新一批来自国外的犹太定居者。
1929年,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成立了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局,集资购买大片土地,出租给巴勒斯坦农村的定居者。租约禁止非犹太人购买或继承土地,禁止犹太承租人雇用非犹太人在这些土地上工作。这些做法都违反当时英国的委任统治法令。
1936~1939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起义之后,犹太复国主义者组建了武装组织,英国官员则公布了更大规模的隔离计划,将整个委任托管区划分为犹太人区和阿拉伯人区两部分。这迫使和平共处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立即陷入了对立状态。
随着二战的爆发,希特勒的灭绝行径使犹太难民挤满了特拉维夫、耶路撒冷西郊和其他犹太人聚居点。无力控制局势的英国,战后将托管移交给了刚成立的联合国。联合国尝试了另一套分治计划,但当时的局势已经表明,最终只有军事力量才能决定双方如何划界。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地区,废除了非军事区,并宣称耶路撒冷再也不会分裂。但以牙还牙已经在地区政治中根深蒂固,此后几十年双方依然冲突不断。奈廷格尔评述道,巴勒斯坦领导人无法在世界上最强大的支持者中凝聚同情,而犹太复国主义者等利益集团主导的强大游说群体一直在华盛顿起作用。和平面临着宗教、反恐和地缘政治的挑战。
“巴勒斯坦激进分子的策略和排他性言论会削弱他们的事业,可能充分表达出许多巴勒斯坦人的愤怒和绝望。但巴勒斯坦激烈的反应也使得新一代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能够自称以色列具有脆弱性,并将这种所谓的脆弱性放到辩论的中心以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特别是美国为了保护以色列的这种所谓的脆弱性,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设置为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的核心敌方。”奈廷格尔指出,让想象力麻木的暴力与报复的循环,为当今世界最复杂且持续存在并由政府资助的城乡隔离制度创造了一个完美的环境。
以色列最终还是将耶路撒冷变成了一座种族隔离城市,用30英尺高(约9.14米)的混凝土屏障和一大片犹太人居住地,将东耶路撒冷其余的阿拉伯人为主的居民区与巴勒斯坦人的城镇和东边其他的城市分隔,阻断了曾经繁密的日常交流。屏障蜿蜒数百里,在整个西岸地区形成区隔。在希伯伦,巴勒斯坦人居住在地势较低的地方,犹太人定居点则在高处。加沙地带也被军事封锁,想要跨界的非犹太人需要获得许可证,并经过漫长等待。
以色列还修建了一套公路网,连通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和西岸定居点,道路系统将巴勒斯坦领土划分为200个独立的区域,其间穿插着以色列军事设施。巴勒斯坦人的道路则与以色列公路系统交叉缠绕,保证不会连通。以色列建筑师埃亚·魏兹曼说,隔离已经有了垂直和水平两个维度,为了隔断以色列山顶和阿拉伯山谷,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了。